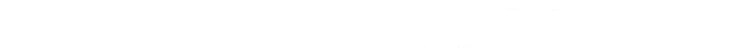221126,股东会议召集瑕疵
裁判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时间:2021年12月
案号:(2021)京01民终9178号
【一审法院认为及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A公司是否曾于2018年6月12日召开会议;二、A公司是否善尽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与召集义务。
对于争议焦点一,虽然A公司提交了B公司与邬某涛签订的《代持及确认协议》,但该协议本身无法证明会议召开情况,且协议中所记涉诉决议系B公司安排他人代邬某涛签署一节恰与岳某林证言中所称邬某涛自主召集并委托其主持、参与股东会会议,以及A公司所称邬某涛已于会议当天签署委托书的情形相互矛盾。加之岳某林曾系A公司员工,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其证言中提到的已作会议记录并有相应表决材料等情节均缺乏客观佐证,则法院对A公司所称曾于2018年6月12日召开会议的主张尚无法予以采信。
对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A公司在明知贾某无法以其户籍地或手机微信收悉股东会会议通知的情况下,以无效的送达手段发送通知,并未善尽通知义务,未能完成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与召集,即便A公司确曾在2018年6月12日召开会议,该会议亦系股东贾某毫不知情的、其他股东的会晤,而非依法召开的股东会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之规定,股东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故,涉诉决议并非在依法召开的股东会会议中作出,应属不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确认2018年6月12日的《A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二审法院认为及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A公司所称2018年6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本案中,就争议股东会决议的成立所依据的事实,A公司应当提供证据,并将其证明至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法定证明标准。若A公司无法完成其证明责任,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关于A公司是否于2018年6月12日召开股东会的事实,A公司提交了公证书、股东会决议、会议记录复印件,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但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未能将该事实的存在证明至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
首先,A公司所称2018年6月12日当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载明该次股东会会议由邬某涛召集和主持,并显示有“邬某涛”的签字,其文字含义应当理解为“召集和主持”的行为系由邬某涛作出。但A公司、邬某涛均认可邬某涛的名字并非本人签署,岳某林证言中所称由其代邬某涛主持并代邬某涛签字的事实过程,与股东会决议所记载的内容不符。
其次,《代持及确认协议》第二条(二)显示,2018年6月12日A公司的股东会“乙方签字也系由甲方安排人员参加和签署”,即由B公司安排了人员参加会议并签署会议文件。该项内容系B公司与邬某涛对此前事实的确认。但岳某林陈述系因邬某涛临时有急事,其前一天晚上接受邬某涛委托代为参会并签署文件,并未提及B公司对其出席的安排。岳某林的陈述与《代持及确认协议》内容并不一致。A公司上诉主张,岳某林代表邬某涛参加并主持股东会同样是基于B公司的安排,但B公司与邬某涛同为A公司股东,且A公司的其他证据均显示,B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峰亦参加了2018年6月12日的股东会,故在邬某涛临时有急事的情况下,B公司直接安排他人代邬某涛出席并签字并不存在障碍。即使B公司系通过邬某涛作出安排的行为,该项安排的意思理应能够为岳某林所知晓。但各方当事人关于邬某涛临时委托岳某林出席并签字的陈述,均无法体现出B公司主动安排的意思。故对于A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关于会议召开过程的事实。在一审中,A公司明确表示无法找到会议记录等其他会议资料,A公司二审中提交会议记录复印件,并未能就其一审中无法提交作出合理解释,结合该会议记录并无原件佐证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一审中岳某林对于参加会议人员陈述为其与王某峰二人,而二审中的证人陈述为刘某、岳某林和王某峰三人,各证人之间关于参会人员这一主要事实的陈述并不一致。根据A公司提交的《公证书》,2018年5月23日何某生向贾某邮寄了股东会通知及委托书和表决票,并对此邮寄的事实进行了公证。何某生另陈述其保管了会议记录及表决票,对上述其专门经手办理的事项,何某生理应具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但何某生对其本人办理邮寄股东会通知的事实陈述不稳定,对于表决票的形式亦表示记不清楚,却能够明确表述其路过时看到刘某、岳某林、王某峰在开会,与常理不符。故本院认为何某生的证言欠缺准确性,其证明效力较弱。证人陈某所述其工作内容仅涉及会议准备工作及打印会议材料,未经历股东会的召开及决议过程。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考虑岳某林、陈某和何某生的身份及利害关系,本院认为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A公司、B公司、邬某涛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A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召开股东会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基于对岳某林证言与其他证据的审查分析,认定该证言证明力较低,符合法律关于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定。对于A公司所持岳某林证言应当采信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会议召集程序瑕疵是否影响股东会决议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股东会召集程序体现了股东会会议发起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了使股东意思归属于公司的前提和基础。召集对象上的瑕疵将直接导致部分股东无法获知股东会会议的召开,使该部分股东丧失了公平的参与股东会表达意见、投票形成公司意志的机会。在召集对象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即便形成决议,也不能认定为股东会决议。本案中,A公司在向贾某身份证登记地址寄送及通过微信发送会议通知等文件时,明知贾某处于服刑状态、无法接收微信和邮件,且并无证据显示贾某曾同意以上述地址或方式作为有效的送达手段。A公司以上述送达方式向贾某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应视为其未召集全部股东。即使2018年6月12日A公司确曾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亦不构成依法召开的股东会决议。此外,在贾某未收到股东会的召开通知、不能及时知晓股东会召开事实的情况下,其无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期限,行使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权利。因此,对于A公司所持本案所涉会议召开程序的瑕疵不属于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原因、贾某应当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股东会决议属于公司内部决策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尚需依法登记以对外表征,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与法定代表人是否变更并非同一法律问题。故一审法院根据A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确定刘某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无不当,且与本案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处理结果并不存在矛盾。A公司所持一审法院允许刘某代表A公司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同理,B公司与A公司在(2018)京0108民初36027号案件中就变更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问题达成协议,亦不表明法院已就本案争议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进行了审查认定。因该案的诉讼主体、诉讼请求、诉讼标的与本案并不相同,贾某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A公司所持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贾某起诉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A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A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申请再审审查法院认为及裁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A公司主张2018年6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成立,但其提交的公证书、股东会决议、会议记录复印件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确认2018年6月12日《A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并无不当。综上,A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A公司的再审申请。